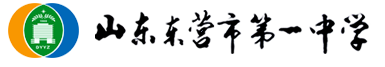嫣红裙
发布人:04级23班 紫色幻影 发布时间:2006-01-12 点击量:
悲凉昏黄的一天。漫天的沙,铺天盖地,风萧萧,水寒寒。在冰冷霜冻的天地间,我捧着血红的衫裙,跪在姐姐的坟前,喃喃自语:
“姐,我为你报仇雪恨了。安息吧。”
泪无声的滑过面颊,滴在嫣红裙上,使那血红的色更刺眼。姐,这是你哀怨的血迹吗?
(一)
公元476年,我和姐姐同降于洛阳的这个没落贵族之家。家已没有过去的荣华富贵,但有了爹和娘的笑声,我和姐姐的童年也确是无忧无虑的。很久以后,大约我和姐姐开始记事时,娘才给我们起了名字。
姐姐名唤若影,我,若离。
娘的笑容暖暖的,倾国倾城,美若天仙。她是有一种清雅脱俗的美丽,一颦一笑,举手投足竟是那样得体而轻盈。我和姐姐最爱看娘拨弦吟唱,一种绕梁三日,韵味不觉可以进入人的灵魂的声音。
娘,是美丽的。
但我一直不晓得,为何她的双眸里有若隐若现的悲伤和哀怨。我也同时发现,只有爹唤她“紫渊”的时候,那丝悲忧的光才会彻底消失。这时的娘更美了,眼睛是那样的明亮,笑容是那样烂漫,暖暖的气息覆盖在世间。
当日子悄无声息地从指尖滑过时,我突然发觉,姐姐的性格是继承了娘的多愁善感的。她也常常静静地凝视着远方,默默地泪流不止,没有人知道,泪为谁流,怨因谁而起。只有我,心疼地为她拭去串串玉珠,想尽一切办法只为她能有一个暖暖的笑。
姐姐总是迫不及待地笑给我看,告诉我没事,可此时此刻的她,眼里的泪花还是盈盈欲坠,我从那憔悴、令人怜悯的美丽脸庞上,看见了忧愁苦闷的影子。
姐姐和娘究竟在愁什么,无人知晓。
所有的人都告诉我,我和姐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,只是,我不会因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而忧郁,也不会因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而愁闷,仿佛所有泪水都赋予了姐姐,而我却夺去了所有的快乐。
很久很久一段时间,如果家里没有我在,一定是哀叹声不断,阴沉昏暗的。
爹说,女娲造我是为了拯救娘和姐姐的苦的。
我一直记着这句话,我边笑边在心里狠狠地记住:姐姐是我的全部,我要把所有的幸福和快乐都给予她。
二
很长一段日子里,我们的生活是平淡而又幸福的,娘教我和姐姐琴棋书画时,爹也安祥地坐在旁边微笑着注视我们。
九岁,刚刚告别懵懂的年龄,我知道这时的我和姐姐已不再是小孩子,我们已无法找出在街上疯跑的理由,我们必须呆在深闺里,弹琴给自己听,刺绣给自己看。
但满城的人都传遍一个消息:李家有两个九岁的小姐和一位风华绝代的夫人,皆美若天仙。
每次爹从街上回来,总是满脸的喜气,爹不是个虚荣的人,但人们的赞赏和夸奖总是可以撩人心的,可姐姐却曾偷偷地跟我说,爹的脸上不是高兴的表情,而是一种深深的忧虑。
太和九年,孝文帝颁布均田令,我们这才从爹那里得知,孝文帝是在平城,他和我们不同,他是鲜卑人。
姐姐惊恐地问爹,鲜卑的天下,允许汉人存留吗?爹总是深邃的看着我们,无语。
我倔强地插嘴,天下是众人的,岂能鲜卑一族所占有。姐姐总是小声地说,若离,少说几句吧,隔墙有耳啊。我不服,但怕姐姐生气,还是住了嘴。
爹每逢此时,都会意味深长地看我,然后起身,背对着我说,若离,你投错了胎,你本应是个男子啊。
我疑惑地想追问,娘却用坚定而温柔的眼神止住了我,家里的气氛变得奇怪,仿佛有大难临头的预感。
深夜,我经过爹和娘的房间,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谈论关于鲜卑和汉的事,我好奇的停下脚步。
“紫渊,拓跋宏不会一直呆在平城的,那里环境恶劣……”
这我知道,很久以前听过一首歌谣――
“悲平城,
驱马入云中,
阴山常晦雪,
荒松无罢风。”
我静下心,听爹和娘还说些什么。
“……鲜卑人迁都是必然之势,你……”是爹的声音。
“老爷,要不咱们走吧,离开洛阳。”
“不,你真以为逃过今天,明天就会平平安安吗?以拓跋宏的性格,他会想方设法找到你的!紫渊,你想想,他怎么会明知自己的妹妹在洛阳而无动于衷呢?!”
妹妹?我惘然,难道娘,她会是……
“老爷,不会的!他怎么会知道我在洛阳呢?平城离洛阳这般遥远,他不会知道的……”
“紫渊,我从街上回到家中的表情瞒住了影儿和离儿,难道你也被瞒住了吗?满城的人都知道,李家的夫人不是汉族女子的模样啊!”
娘在小声哭泣,许久,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我满心的慌乱,悄悄地穿过长廊,直走向姐姐的闺房。急促而轻轻地敲门。
“若离?”姐姐打开门,惊奇地看着我,“为何这么晚还不休息?”姐姐说着,爱抚地拂掉我肩上的落叶,“你去了哪里?”
“姐姐,我有话对你讲。”我拉住姐姐的手,一脸的慌恐。
姐关切地说,离儿,不早了,有什么话,明早再说吧。
“不。”我使劲摇头。
我把听到的一股脑说出来。姐姐开始是有些漫不经心的,既而是疑惑和异样的表情。姐姐慢慢起身,缀着蓝流苏的裙摆拖在地上。姐姐第一次这么严肃地看着我,她像爹一样转过身背对着我说,离儿,你全知道了。
我诧异地猛一抬头:“姐,原来你……”
姐忧郁地点头:“这些我早听说了,是娘无意中说漏嘴的。”
我和姐姐无语地坐着。
姐姐突然起身,拉起我的手,离儿,快回吧,娘和爹的事,我们还是不要管太多吧。记着,少说几句,隔墙有耳啊。
我看到了姐姐紧皱的眉头,我看到了姐姐苍白的唇。
回去的那一夜,我辗转难眠。
(三)
太和十四年的一天,我突然在爹的头上发现了一根白发。爹老了,那乌亮的发中竟也有了银丝。
爹看着我拔下的银丝,沉沉地说,若离,你要像深闺里的小姐才好,怎能这样肆无忌惮呢。
我调皮地说,爹,你不是说我本应为男儿么。
忽然爹哈哈大笑,狠劲地拍我的背。我痛得差点失态地跳起来。爹静静地看我,若离啊,你看你哪里承载得了这些重压呢,爹的巴掌拍一下你都会疼。
爹严肃地转过身:若离啊,还是听你娘的话,做文静乖巧的小姐吧,能有若影的一半温柔,爹就放心了。
我还是调皮地笑,爹,我不,我要坚强,我要保护娘和姐姐。爹沉默。
霎那间,觉得爹老了很多,他的身躯已不像原先那般高大挺拔了。
十四岁,会有足够的快乐吗?
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,我和姐姐随娘去屋后的河边洗衣。娘是个爱水的女子,她久久注视着河上的柔波和水面上泛起的圈圈涟漪,嘴角翘起一个很美很优雅的弧。娘用纤细的手指轻轻拨着清凉、明澈见底的水,那白嫩的皮肤,那修长的指甲插入水的柔波里,摇晃摇晃……
我和姐姐呆呆的注视着娘——她的美如白荷出水,似月夜玉兰。
娘似乎注意到了我和姐姐傻傻的模样,冲我们淡淡一笑。“离儿!”娘冲我招招手。
我蹦蹦跳跳的跑过去。娘嗔怒般对我说:“离儿,难为你了,拖那么长的裙衫还跑得起来!”姐姐和娘都笑了起来,她们的声音是那样像,一样的温柔,一样的清新自然,一样的悦耳动听。
我调皮的跑到姐姐后面,边用手捋姐姐柔顺的及腰长发边对娘说,娘,叫我做什么吗?
娘走到我们旁边,坐下。纯白的裙在风里摆动。娘静静的看我们。她离我们是那么近,我可以在娘明亮的双眸里看到我和姐姐,我们长得几乎一个模样,但我多了一分调皮,姐姐多了一分温柔。娘抚摩了一下我的发,淡淡的笑,我看到了忧怨的影子。姐姐,也看到了。她暗中捏了一下我的手指。
“影儿,离儿,如果有一天,娘离开你们……”
“我不许!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强烈的脱口而出。
娘的表情很尴尬:“不是,我是说如果……”
“娘,我不允许有‘如果’发生。“我很认真的看着娘。姐姐轻轻拍了拍我的肩,离儿,你先让娘说下去吧。
娘用试探的眼神看着我们,轻轻的继续说:如果我有一天离开你们,你们要答应娘替我好好照顾这个家,还有,要听爹的话……
离儿,你和姐姐都十四岁了,娘却偏偏放不下你。不要这样调皮,要学着若影点,沉稳些……
还有,你们要记住,少说几句,隔墙有耳。更何况……红颜薄命!
我猛的转头看姐姐,张口问,什么叫红颜薄命?
姐和娘都安静的看我,悲伤的情绪布满整个天地之间,耳边的流水声好似已停止,潺潺的声音销声匿迹。
风吹过,我不冷,却打了个寒颤。
姐抬头看娘,娘什么也没说。突然间,她用从未有过的嬉笑口气和不知要比平常大多少倍的声音说,娘是在说如果,也许根本不会发生,看你们俩紧张的样子!哈哈哈——
娘从未这样大声的笑过,她在掩饰自己,因而一直低头搓衣服,不愿抬头看我们。
我惊恐的想要问些什么,姐姐却又用她那坚定而温柔的眼光把我止住了。
我无语。姐无语。娘笑过后也无语。
于是空气又像凝固般成为定格,它难道想留下这一幕吗?不!不要!我不要这虚伪的一幕!我不要这难听的用来掩饰的笑声!
但从那一直到回家,娘和姐姐都没有说一句话。只有我一个人唧唧喳喳的讲个不停,却也是些不痛不痒的琐碎事,因为,我其实也没心情。
看来,空气真的要留下那令人厌烦又觉悲凉的一幕了。
随着柔然的强大,再加之在平城实在难以控制南方,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。
洛阳,一个让拓跋宏魂牵梦绕的城。他知道,那里有他那倾国倾城的妹妹。
然而,孝文帝深知这并非易事,便在朝中说要大规模进攻南齐。满朝文武哗然。尤其是任城王拓跋澄,孝文帝万万没有想过,他会反对得这样强烈。
夜深人静。
孝文帝在宫中召见任城王拓跋澄。孝文帝微微一笑,说:“任城王为何这般强烈反对进攻南齐?”
拓跋澄用他那深邃的眸子坚定地看着孝文帝,一字一顿地答道:“臣以为,这并非上策。陛下进攻南齐怎可在此季?未免操之过急。请陛下三思。”
孝文帝在低头站立的任城王面前来回地踱着步子。突然孝文帝在座椅前停下,缓缓转身,用他那浑厚的嗓音道出了进攻南齐的真正原因:“朕想迁都洛阳。平城地势、资源均显滑坡趋势,且柔然逐渐强大,迁都是必然之举。只是,朕深知众大臣中必有许多像你不同意进攻南齐一样强烈反对迁都,故用此计。”
任城王猛地抬起头,眼里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:“以陛下之意,要迁都洛阳?”
“正是此意。”
任城王突然下跪,孝文帝内心一紧。
“陛下英明!臣等罪该万死!”
孝文帝会心大笑,任城王也陪着爽朗地笑。
孝文帝始终没有讲到关于公主在洛阳之事。但不想,任城王提到了。
“陛下,据臣了解,公主在洛阳。但详情确是一无所知。”
孝文帝忧郁地注视着任城王,缓缓吐出几个字:“是,朕已知道。”
“陛下为何不派人接公主回宫?”
孝文帝苦笑:“以萱儿性格,任城王以为,她会回宫吗?”孝文帝慢慢仰起头,深深叹了一口气:“朕想到达洛阳时再说,万一行动鲁莽,萱儿怕是会提早离开洛阳。”
任城王一言不发地站着,眼光的深邃让人担忧。
“如无他事,臣先行告退,陛下?”
孝文帝背对他,摆了摆袖子。既而,陷入沉思……
“萱儿,宏儿!小心别摔着!”母后身边的他们曾是那样无忧无虑,天真烂漫。
“哥,额娘不让我们乱跑!”萱儿可爱的脸蛋仰起,小手紧拽着拓跋宏的衣衫一角。
“不要紧,咱们声音小一点。你看!那只小白兔就在那里。萱儿,你不想要么?”啊!那么可爱的白兔!圆滚滚的身子,毛绒绒的好似一个小圆球。萱儿太喜欢它了。
拓跋宏猫着身子,猛地扑了过去。“抓住了,抓住了!”两个天真的孩子都拍手叫了起来。
“哎哟哟!我的小祖宗!你们怎么逃到这里来了!哎哟哟!身上脏成这个样子,你们让我怎么向皇后娘娘交待啊——”公公发现了这一对淘气的兄妹,又是好笑又是恐慌。
拓跋宏和萱儿相视而笑,牵着手趁公公不住地说“都怪我”的时候,抱着小白兔跑得无影无踪……
“陛下,有什么要吩咐奴才的吗?”公公不知何时进了屋。
孝文帝回过神,还是不耐烦地挥挥衣袖。公公悄悄退下。
“宫中的一切是如此辉煌、炫丽,萱儿,你为何选择离开呢?”
孝文帝边自言自语边看着妹妹留下的唯一的东西——一条殷红色的裙子。他知道,这不是萱儿故意留下的。她想带走一切,只是,这条裙子无法塞进已很鼓的包袱。孝文帝至今也未弄清,萱儿为何要出宫,又怎样躲得过这么多侍卫的眼,冲到宫外的。
萱儿,你一定不要离开洛阳啊!一定!!
淫雨在户外哭泣着,瘦叶在百合窗前瑟缩着。一个冰冷的天气。
爹还是那样的早就出去了。娘和我们坐在窗前绣一件紫衣上空缺的炫丽的羽毛。我们边做活边听娘讲女娲造人的故事。我和姐姐已听了几多遍的陈旧的故事,从娘的口里说出时却一次又一次地拥了那种神秘和美好。
不禁又回忆起九岁那年爹对我说过的话,女娲娘娘造我,是为了保护娘和姐姐。
这些年来,我却总那样调皮,但在“顽劣”的性格下,我一直在坚守着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。
但十四岁的我,不知道自己的使命会马上破裂,变成碎片,飘得无影无踪。任凭我怎样哀诉,都找不到它们的痕迹。
当温暖的屋内充满着快乐的气息的时候,当窗外的雨还是连绵不断的时候,当刮风的声音还是那样萧瑟的时候,突然间,屋里的温馨和祥和被破坏。门开了。冷风猛地吹了进来,密而细的雨丝斜斜地射入。
娘和我们都不约而同的停下手中的活,向门口望去。门外的嘈杂声盖住了风的呼啸。娘起身走到门口,风把她那整齐的发髻一下子给吹开了,发散了下来,如瀑布般“流动”着披在肩上。粉白色的裙带被风扬起,飘得好高好高。我和姐姐不约而同的“哇”了一声,传说中的女娲有娘这般美丽吗?
我们没有跑到门口,因为爹和娘吩咐过,有客的时候,是不允许我们出面的。
听见娘在门外和来客说些什么,但风的怒吼盖住了娘的温柔而偏低的嗓音。我们什么也没有听清。
突然,“哗啦啦”一阵响后,我们听到娘很高很努力的吼了一声:“松手!”我紧张地看着姐姐,想过去。姐姐紧紧攥着我的手,不允许。我依偎在姐姐旁边,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我们两个“怦怦”的心跳。
娘终于走了进来,我看到了她浮肿的双眼。娘哭过。
“娘——”我叫。
她轻轻按住我的唇,微笑着说,影儿,离儿,娘要去趟瑶光寺,今日是个祭祀的日子。影儿,我很快就回,好生带着离儿,等你们的爹回来。
娘的声音在颤抖。眼圈又红了。
我突然叫住已走到门口的娘:“娘,外面冷,多穿些吧!”我边说边扯出红木箱里的短袄递了过去。这次,我真真切切地看见了娘脸颊上的泪光。娘默默摘下腕上的银镯子,小心地戴在我的腕上,娘的手冰凉冰凉,我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。
娘定定地看了看我和姐姐,然后走了出去。依稀间,看到门外有戴那种宫帽的人。门外渐渐恢复了只有雨声和风声的平静。
天还是那样阴沉。
我蜷缩在姐姐旁边,紧盯着娘的那只银镯。突然感觉有冰凉的水顺着我的脖颈滑入衣内。我抬头,姐姐悄无声息地哭着,珍珠一样的泪珠在她红红的眼圈里徘徊。
我也想哭,但我不能。我的降生是为了保护娘和姐姐。我愣是把快要掉落的泪挤了回去。我要坚强。
娘真的是去瑶光寺祭祀了吗?怎么不记得往年的此时也有此事?娘刚刚是同谁一道去的?那些戴宫帽的人又是谁?他们是宫里来的人们?那他们是所谓的鲜卑族的吧?那娘岂不是……我猛地停止了疑问,我不住地在心里骂自己,胡想些什么?娘不过是去瑶光寺了,娘去瑶光寺了,娘去瑶光寺了……
不知不觉中,我被门的响声惊了一下,缓缓张开疲惫的双眼,才发现自己在姐姐的身旁睡着了。姐注视着门口——爹回来了。
雨不知何时已停,风也收敛起它的吓人的声音。我猛地扑到爹身上。“爹!娘她……”
爹手里的东西“哗”掉了一地。
他扶住我,紧张地看我。爹深黑的眸子里有一丝惊恐。
姐跑了过来,轻轻摇了摇爹的胳膊,温柔地说,爹,娘去瑶光寺祭祀了。爹长舒一口气,把我扶到床上,帮姐姐拾地上的东西。我心里一阵愧疚。我的胆怯,我的恐惧全都泄漏了出来。
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心里的那个信念——我要保护姐和娘。
爹收拾完东西就准备离开。他说他去找一下娘,让我们好好呆在家里。叮嘱着和娘一样的话,不许我们离开。
我和姐姐都忽然间懂得了些什么。
这是一场噩梦,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梦。
从那天起,我们的家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破碎了,因为爹和娘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曾经美丽的屋子里。
一个月色溶溶夜。任城王在府内准备就寝。一个小卒慌慌张张地闯进,一下子跪在地上:
“王爷,洛阳那个貌似鲜卑的女人被我们带来了。”
小卒的脸上布满了快乐和殷勤的笑。
任城王心里一震,命其速将那女子带到正厅。
正厅里,辉煌依然,只是比皇宫里少了几把龙椅。金黄色让人感到刺眼。任城王注视着跪在地上小声抽泣的女子,有些泛着黄色的发零乱地披着,头发很长,垂地。她身穿一件充满鲜卑特色的短袄,以这点,也可以确定她的身份了。女子低着头,无法看清她的面容。
任城王沉沉的声音传出:抬起头。
女子撩了一下粉白色的裙带,又从容地整理了一下她零乱的发丝,抬起头。一双美丽而充满哀怨的双眸。
任城王看清了她的模样,呆住了。不是因为她眉黛轻颦,莲脸生春,而是因为这是一张曾经如此熟悉的脸。
既而,任城王被女子脖颈上配的金锁反射的光刺了眼睛一下,这……这不是冯太后给予陛下和公主的救命锁吗?难道眼前的真是……
任城王慌忙走到女子面前,双手扶起她,待她站定,便直直地跪了下去:“公主,微臣给公主请安。”
女子的眼光不再错乱和迷惘。她明白了一切,她知道自己在哪里了。温柔的声音和坚定而有些仇视的目光一起射向任城王,任城王请起吧,我哪里是什么公主?小女一介草民,仅此而已。女子背过身去,不再言语。
任城王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:若您并非公主,怎知微臣是任城王拓跋澄?微臣马上派人禀告陛下。
任城王慌张而惊喜地站起来,向看呆了的小卒挥了挥手。
“慢着!我不是公主,你们都听着,我不是公主!!”
但任凭女子怎样喊,小卒还是飞奔般跑出去了。任城王命侍者帮公主洗拭整理,女子一反温柔的常态,双手推翻了水盆。泛着金光的盆“咣当”掉在了地上,声音震得人发晕。女子欲哭无泪。她终究又回到这里,一个让自己决定终生逃离的桎梏之地。
“陛下驾到——”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。女子心里震了一下:相隔了这么多年,自己竟然还可以如此清晰地分辨出哥哥走路的声音。
眼前一亮。威武的装束,浓浓的剑眉,还有额间的那颗红痣,哥一点都没有变。孝文帝双手向前伸着,似欲抓住什么,激动地喊了一声:“萱儿!”
女子的脸上滑下一颗颗泪珠。她毅然拭干了泪,轻声说,陛下和任城王都认错人了,我不叫萱儿,我叫紫渊。
“萱儿,你怎么可以这样绝情?额娘走后,你也躲到宫外,这都究竟是为何?”
紫渊紧紧握着粉白裙带,尽量使自己变得平静。她略思片刻,还是那样温柔地答道:“我不要禁锢,我要自由和快乐。我已经习惯了世俗的平静,已经不会再做任性的华贵的公主了。陛下还是让我在宫外安静地活着吧。”
孝文帝的泪直直地掉落,一滴,两滴,三滴……
紫渊突然笑了,记得小时候,每逢自己哭,哥都会用绵绢帮她擦得不留一点泪迹。紫渊笑着,却一点儿不知道,咸涩的泪滑进了嘴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