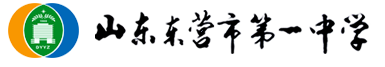流言――日落的悼念
发布人:高2003级06班 李焱 发布时间:2005-06-16 点击量:
忘记了什么时候才听懂爸爸叫我林秋。我明白,我是他,他是我,林秋的想法和动作也就是我的想法和动作。一种很荒唐的认为,既使有千万种嘲笑的理由,我最后还是那么去认为了。这也很可能是我在学会感觉事物之前沉淀下来的难言之隐,因为觉得没有继续埋藏的必要的,所以它被我捧将出来见了世面。
映年说:“你不会觉得这很狭隘么?”是啊,它真的是狭隘啊,在一间黑窄的小屋里存放的东西,突然将它搬到外面来,面对这豁然的一切,明白开始不知所措了。
那更广阔的空间呢?比如说宇宙,一个放眼而望不尽的地方。到达那里,这里的一切也都将变得狭隘了,所有的看法和认为。
即使如此,我们却仍旧在找寻,希望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会明白,我们在这里的真实意义,映年说这除非能到达那片深远的宇宙,那片永远也没有日落的世界,我们的思想才不会像云彩一样,鲜红过后,又迅疾的灰沉下去。曾经目睹过这样的画面,仿佛没有过程,所有的变化都好像在一瞬间一蹴而就。想留住什么却力不从心,于是只有放手。
那个夏天对于映年来说有种特别的意义。日光把整座城市的喧嚣照亮,仿佛什么都是从这一天开始,什么都是从这一天回归往昔,轮回通道的大门被某种力量突然打开,记忆在一阵汹涌的泛滥过后显得异常平静,只有两个在野地里奔跑的孩子,踏过一片一片倒伏的青草,你追我赶,我折断的一株向日葵,给你。你掰下的一株芦苇棒,给我。
这都是我与林秋所共有的东西,然而仅仅是一部分,也不可能是全部,我们的梦插着不同的翅膀,所以将飞向不同的方向。即使等到哪一天有一个飘散了,另一个也只会拾起羽毛,把它带到曾经走过的那个路口,林秋是一个这样的孩子,他说他是林秋,你是映年。
我是林秋,你是映年。一切都想象着说完了,那个夏天,妈妈说,你该去上学了。
映年也跟着我上学,所以我们看到早晨太阳让窗框留下的影子,棱角分明,映年说,你看见它在缩短吗?我摇头,仿佛这也是一个没有过程可言的事情。果然,正午没了树影,土块的褐色尽情的显露出来,映年说他很开心。因为他,我也一样。
有一阵子我们就倚在那棵长满桑葚的树下写作业,总是不想回家,回到那间几十平方米狭小的地方。直到夕阳灿烂过许久,最后连那个红蛋蛋也在天边消失不见。心中仿佛打碎了什么。作业写完了,笔却没有停驻,它依旧在纸上点点画画,空白里出现一些无规律的曲线,也许在预言着什么什么。
映年通常都是要在我家里坐一会儿才走的,于是他也就无辜的听着妈的训话,有一些一直听了几年,几年都没有改变,映年对我说你不要觉得不幸,我每天要听两遍。于是我拍着他的肩膀,看见身旁的花朵枯萎成一片深紫色,浓得仿佛要滴下血来。血是什么做的呢?当我第一次流下血来的时候,我便这样的去问映年,因为还小,于是我们俩乱猜一气,直到把世界颠倒。现在想想为什么,也只是觉得当时快乐,快乐得难以言语,或许这样就叫做不可言传,当所有的感觉都变得如此,我也应该去习惯意会。
记得第一次产生感想是听映年的妈妈讲故事,她说,当女娲把一团泥巴附上灵气的时候,便有了现在的我们。那灵气该有多少?何时耗尽?它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的泯灭,那么现在的我们或是以后的人们,会不会又再变回一团泥巴?映年的妈妈岔开话题,我也没有再纠缠下去,因为某种感觉告诉我,它是一个荒唐而难以解决的问题,不放下,或许就要一直拿到生命的终结,最后,去问那片无所不知的宇宙。
几年级的自然课中曾提到过那片地方,老师说,它在冰冷中膨胀。我看见映年在座位上笑了,下课后我问他为什么会笑,他说,我知道他是有生命的。他容纳了古今之人的归宿,他让人们的灵魂安静地居住在那里,住在我们眼中的那片神秘的世界里。映年很少会如此的开心,但这一次,他真的开心的流露出来了,仿佛找回了失去很久的东西,一个属于他的东西。
笑过之后窗外就下雨了,一阵明亮过后又暗淡下来,我知道这是在打闪,地上的叶子也浮起来,它想漂到更远的地方去,于是就漂走了。雨水打消树木疯长的情绪,画面灰暗,颜色失去了鲜艳亮丽,失落的站在空地上四下张望,它执着于找回,雨却愈下愈大,直到淹埋了它的身体,最后连呼吸也听不到了,除了雨声,一切寂静。
我和映年一度喜欢去倚在窗子边看雨,外面朦胧一片,眼里也一片朦胧,视觉无法伸展,听觉却温柔起来,雨点讲了许多关于精灵的故事,纯洁,死亡,飘摇的年代。
我们走上高中。
日子在这里有了注音,它已经不再去管那些绿过一年又一年的夏天。每个人都在四季里皱了眉,写过一本《创新设计》,又写过一本《绿色通道》,在周围所有的人有了信念,他们说,题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映年问我这可笑么?我放下书无言以对。
夜终于黑得不见了霓虹,这代表什么?初冬还没有第一场雪,于是人们开始等待,等待着纵情于雪中而奔驰的一刻。班主任上台说按成绩调位,映年就这样被丢在角落里,我看见,太阳终于西下。他说,在那里可以清楚的看见夏天里死去的花,被逼迫得掩埋到泥土里。
我说那有意义吗?他说有的,它的意义在于警训。
初冬的第一场雪是在圣诞节那一天才迟迟而来的,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俯在窗子上看灯下雪花的飘影,仿佛迷蔓了古龙的一切,在天空荡漾许久,终于在这一天飘落下来,带着原有的思想和灵魂,像一场盛大的死亡仪式,映年说那些是冤魂的碎屑,看哪!如此之多。
过后便是期末的家长会,映年站在一旁不出一声,最后他的妈妈步履沉重的走过来把人从我的身边带走,也是不出一声,映年向我挥手,我也不出一声。
晚上,映年妈妈的声音很大,近乎歇斯底里的吼叫,我望着钟表,思绪却全都臣服于墙后的声音。
你也真对得起我,我这么把你拉扯大你就这么对我,你是不是也太过分了。你考不好,人家怎么就考得好!我让你在学校里混……我想写作,这也不行吗?……写?我把你手打断看你还写个屁……
突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,心跳也附和着漏空了一下,挂表又恢复了声响。
我把头伸出窗外想去看看窗下的野兰,却发现所有的色彩都被泼上了浓浓的墨黑,最后连自己也沉浸在里面,亮着灯也无法摆脱。当我认识到这些都是徒劳之后,于是我缓缓的躺下去,让身体在这里面得以放松,的确是一种舒服的感觉,深掩在退缩之后,没有了执着的刀锋,画面温柔。
不一会儿门铃便有了动静,打开门看见映年站在外面,他说今天晚上在你家睡可以吗?
晚上映年睡得异常的安静,胸前的起伏开始温柔起来,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,仿佛整个人睡在了一个没有动荡的朝代,梦见一生快乐。
往后的一个月我再没有见到映年一面,后来我才知道他转学了,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,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,学会“很远”这个词语的时候就无法弄清楚具体的含义,只知道那是一个难以到达的地方。
八个月后,我竟出奇的在校门口看见映年,我说映年你回来了,风吹落一滴雨点儿,随后大雨便倾泄下来,周围是人群的呼喊,眼前的一切开始慌乱起来,映年也慌乱起来,他说,我走了,我真的走了,再也不回来了。
随后,映年如梦一般的在我的眼前顿失,我轻声的叫映年,没有人答应,可眼前那片雨帘的背后,却似乎还晃动着人影。一个渐渐远去的熟悉的背影,世界白亮一下又迅速暗淡下去,一道闪电,打消了所有的记忆。
回到家后我去找映年,我敲了他的房门,他说我累了,想睡了。
就像曾经在电视上演出一样,映年在屋里没有了动静,耳旁忽然轰的一声,惊了一下,原来是电视里的大船沉没,所有的人都变换了映年的声音,他们叫喊,林秋,林秋……
我推了推门,发现门根本就没有锁,屋内异常的干净,窗外树头的黄叶被雨水打得依稀可见,映年在床上睡得很沉,白色的床单上浸透了殷红,手腕上伤口的血已停止了外溢,他的眉头也在这个秋天里随着心跳的停止舒展开了。他真的留下了以往的脸孔,带着幼时的面容离开了,正像他说的,我走了,真的走了,再也不回来了……
一年以后的今天,我帮他写完了他的散文日记,在这秋季的日落之时,我又来到他的坟前,虽然这里装的只是一具尸骨,但是我依旧又来到这里。
你在宇宙,我在地球,你也许能看到我吧,我这么想。
秋天又恍恍惚惚昏昏沉沉的踱到我的面前了,人们依旧的沉醉在其中,执着的沿着一条拥挤的路走着,有一天我突然的发现树上的年轮又徒然的多了一圈,这难道也是一件没有过程的事吗?你在那里看到了吗?这里的真实意义。
我知道一切都无法替代回答。太阳又在西边没了影儿,我在这片深爱过的秋林里为你悼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