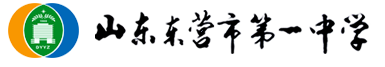自由区(下)
发布人:血大林 发布时间:2007-12-01 点击量:
[三]
村南边有座古宅子,听阿娘说,那是明朝留下来的,叫“莲花庙”。庙里的老和尚得了灵气,一天晚上,正悟禅打坐,感到心中不快,便呕吐不止。妙哉,最后吐出一个顶小的莲花,在晚上都亮得刺眼,方圆十里的有灵性的畜牲,都在子时不约而同地冲天高嚎起来。莲花芯子听说是金舍利,有起死复生、长生不老的奇效。当时明朝的一个大官听说了,便起了贼心,晚上派了几个山匪,将老和尚杀了。结果,金莲愤怒了似的,发出强光,便地动山摇,六月飘雪。几个山匪便磕头谢罪,最后吐了几斤鲜血而死。那大官也突然胸中有震烈之痛,吐血而亡。金莲便飞到了庙里的墙上,成了庙里的花神,老和尚化作仙狐,守护金莲。
两年后那晚,我跟二狗来到庙里耍闹。这是一座荒芜了的宅子,外围的墙上爬满莲蓬和何首乌,上面的蝉子放肆的叫,各种虫子也应合着,给这院子更添了一笔荒芜。大门紧锁,锈迹斑驳但盖不住曾经的伟岸。围墙上有一个窟窿,但被何首乌的藤缠得不透风,里面外面就就此隔断了。
二狗在墙外面手脚并用,奋力地想爬过去。她太笨了,半天也没有什么效果,墙壁也被她扯得烂乎乎的,土阵阵往下掉。我说:“你咋不抓住树藤呢?”她抓住了藤子,双脚向上蹬踹,“嘶啦”一声藤子挣断了,二狗掉在地上,先愣了一会儿,接着不知所措地哭起来。我上前瞧见她的手,有好几道树藤勒的血痕。月光映得血迹也微微泛亮。突然,我心里不知怎的,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,就像上次阿爹摔坏了腿,我见到他痛苦的样子,心中有种酸楚的关怀的感觉,却又不知怎样表达。
二狗哭咧咧地说:“咋办,阿岗,我进不去了,我拿不到金莲了。”
“拿金莲干啥?”我蹲下身一壁看她的手一壁说。
“金莲能生男娃,如果我阿娘吃了金莲能生男娃!阿爹说生男娃我就不嫁给小毛子,我就不嫁给小毛子!”二狗激动得瞪大眼睛,脸也扭曲了。在月光下,显得十分吓人,活像罗煞夜叉,张开血盆大口,愤恨得活活要吃了我似的。
“你咋知道你要嫁给那个瓜子?”我问。
“那夜你走后,我在外屋烧水,回里屋时便听见阿爹和阿娘谈着这件事。我还是个人不?为啥家里穷要我为此往火坑里跳,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我就是他们像阿猫阿狗一样的玩物,男娃到底好在哪里,男女到底有什么区别,我该咋办啊,阿岗。许是我晚上不安静睡觉,许是那天我摔坏了家里唯一的大瓷盆,许是小时候拿锄头锄坏了地里的菜苗,我也不知为啥,女娃就比男娃轻贱这么多吗?”
听了二狗的话,我无言以答。我先是惊讶,这八岁的闺女怎讲出这般话来,这女娃怎的这般苦命;随后又有一阵恐慌浮上心头,我怕,若是我是女娃,阿娘也会不会送我作童养媳。我开始怜悯起这女娃,心想一定要帮她。
我振奋了一下自己说:“二狗,找把镰刀,割断墙洞上的何首乌。”
“我阿娘说里面有美女蛇,你若是与她眼睛遇着了,就定在那里,美女蛇就用身子卷死你。”二狗有点怕似的说。
“我阿娘说是仙狐,不是美女蛇。哎,不管是啥,咱都得进去!”
“阿岗你看。”说着二狗拾起一块一面较锋利的石片对我说,“用这个也可以割烂了那藤子。”
二狗走上前拼了命地用力胡乱割着树藤,还一壁用手撕扯着,像只发狂了的野兽,宣泄着它的愤怒。
藤子割烂了,我跟二狗钻进去,深陷在杂草丛中。里面果然有一座宅子,颓垣微倒,也果然有蛇,但却不是美女蛇,只是那种普通的草蛇还有草生动物相互纠缠着。我们穿过高草丛,长枝叶扫过我们的脸微微作痒,有时还踩到大虫子一响一个“啪”。
宅门没有上锁,微开,手往门上一扶,“几尺厚”的灰尘被扫下来让我咳了半天,蜘蛛很是自由自在地在两扇门之间爬动。二狗和我一齐用力,使出吃奶的劲儿推开那嘎吱作响的破门。果然,那金莲深深刻刻地贴在墙上,在月光的照耀下更显明朗。二狗见了,“扑通”一声跪下,双手闭合,嘴里开始嘟囔:“求求金莲大仙保佑我阿娘生男娃,不要让我嫁给胡阿毛……求您显灵,让我阿娘吃了您的金舍利。”二狗见没有动静,还以为是金莲怪罪自己,便开始磕头。一共磕了二十四个响头。见金莲还是没反应,又磕了二十四个响头。不知这样反复了几次,二狗瘫软在地上,恸哭起来。我起身去扶她,她说:“咋办,阿岗。没有金舍利,我……”我抱着二狗,有一种十分怜悯的感觉,她这样脆弱地倒在我怀里,我觉得我应该顶起她撑不起来的那一边。我便也虔诚地跪下磕头,求金莲大仙显灵,虽然我对这个深恶痛绝。
折腾了一晚,所谓的金莲也没有显灵,所谓的狐仙和美女蛇也没有出来作乱。我和二狗倚在墙根儿,绝望的痴痴看着天亮。
几天之后,我去二狗家应她,只见一个嘴边长着媒婆痣的女人,盘着腿坐在她家炕上。
二狗一声不吭地站在屋里,微微抽泣。她爹坐在门坎儿上闷闷地抽着旱烟,她娘哭着,一壁照顾怀里吃奶的孩子,一壁看护着两岁的女娃。
长痣的女人开口了:“我崔巧芬儿可是远近闻名的媒婆,这次也为了村长大人向你们家提亲,竟受这般的窝囊气!我说二狗的爹,你就这么不知抬举,先前答应了人家,如今却反悔不嫁,这不是明摆的看我们村长好欺负吗!你若是想好好地在济乡呆下去,就本分点!村长也是全为你们着想,你想二狗这般样子,能嫁哪个好人家呀?村长不嫌弃你家穷,已经是天赐的福了。再说,小毛子就是脑子差了点,但秉性并不坏,不是说‘傻人有傻福’嘛,二狗阿爹,你说是不是?”
“嗯。”二狗阿爹又是一口旱烟。二狗阿娘哭得更厉害了。
崔巧芬瞥了二狗阿娘一眼,歪着嘴,显得她的痣格外好看:“二狗她阿娘,你又生了一胎女娃罢,哼哼。这女娃堆里,怎么能有家里的顶梁柱,你也该明理知趣儿,二狗早些嫁了,你们还会得到村里的补助,以后也好养个男娃。这岂不是好事?”
二狗阿娘也点点头,问:“那啥时候入亲?”
“十二三岁时罢。”崔巧芬又高兴地说了一句,“这样才对吗,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
我实在是忍不住了,上前说:“果然是要识时务!你崔巧芬可就不识时务。”
崔巧芬惊骇了一下,不屑地说:“你是谁?小小年纪竟敢如此无理!”
“陈阿岗。怎的,你不认识我?”
“哪里来的野种,到这里来撒泼!糟践胚子!这里轮不到你骂我!我崔巧芬好呆也是有名望的人,我就算再糟践,也没有你骂我的份儿!”崔巧芬愤慨得满脸暴起青筋,怒张杏仁眼,指着我满嘴喷口水。
“你仗着村长狗势力,来欺负老实人,还算不糟践?你这样逼得人家子散不和,就……就对不起你的祖宗!”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这样爽快地骂。
“你……你……小崽子……”崔巧芬气得不知如何回答,下床便要揍我。她揪住我耳朵,说:“走,找你爹,管教你这个不是东西的东西!你爹是谁?”
“陈大鸿!”我一壁拽开她的手一壁说。
“什么?陈大鸿?”她赶忙松开我的耳朵,“济乡首富?陈大鸿?”
“对,怎的,你刚明白?”我鄙视地说。
“哟,原来是陈少爷呀,我这双浊眼,没认出您的荣姿,怪我怪我,我这张贱嘴,说了不该说的话,请您海涵。您说的对,我不识时务,我不是东西,我怎能认错了您呢?悔不该,悔不该!”崔巧芬弯着腰,向我鞠躬道歉。
“滚!我不懂得什么首富不首富,总之你要是还敢来欺负二狗,我定不饶你!”我斥责道。
说完她便小跑着逃去,走到大门时还回头斜了一眼。
几日后,我从西边的田埂上回来,刚离近家门口,就见胡乃三笑盈盈地从我家走出来,我阿爹正跟他客气。我走上前不理会他,他却主动地扶着我的脑袋,露出金灿灿的刚镶的门牙,依旧假惺惺地笑道:“阿岗回来了,哈哈,在田埂上逮了什么好东西啊?”我头一歪,道:“不用你管!”胡乃三正尴尬着,我阿爹便“啪”给我一记耳光,破口骂道:“你这混小子好不识抬举,真给老子丢人!村长您大人不记小人过,犬子无理,您老海涵。”阿爹一壁推着我的脑袋,一壁说:“快给村长赔不是!”我委屈并愤恨地说:“不赔不赔!”说完跑回了屋里。
我回屋正疑诧胡乃三怎的来我家,阿爹便进屋揪住我的衣裳,抄起笤帚要揍我。我挣扎道:“凭啥打我!”“呸!混账小子,你做的孽还不够吗!”说罢给我一抽条。我忍着痛,驳道:“什么孽?”阿爹举着笤帚头指着我说:“前些日子你去二狗家大闹,竟骂了村长邀来的媒婆,我看你的傲气都快上天了!人家办亲事,你插哪门子手!你办了这等的蠢事,让旁人看,好似我与村长有怨仇,你还要我怎的在济乡混下去!我怎能不打你!”说罢又一抽条。身上的疼使我的眼睛里挤出了泪水,我仍旧不服气:“我就是要保护二狗,我就是不让她嫁给胡阿毛!我要让二狗活得神气舒坦!村长胡乃三那个小人,耍阴腔回我家告状,我决不怕他!”阿爹更气了,紧闭嘴唇瞪着眼打我。我也不挣扎,紧闭着嘴巴任他打。
阿爹命我跪在屋里悔过,尔后,阿爹叹着气,坐在我面前,说:“阿岗,还疼不疼?别怪你爹狠,我也是为你好。”
我傲着头不服。
“唉!你小小年纪,咋知道大人之间为人处事的难呢?胡乃三,我们惹不起啊!在济乡,属他顶事儿,我们都要靠他吃饭,就算我有几个钱,就算这已经是自由区,还是要靠他的政策,他的主意。我也知道把二狗嫁过去是委屈了她,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?阿岗,你可别怨你爹,咱没那个能耐救二狗呀!”阿爹双眼含泪地说,好似哀求一样。
我惊讶了,这些大人们深思熟虑的事,是我从未想过的。没想到阿爹也是个恃强的人,以前在我心中的英雄地位顿时轰然倒塌。望着阿爹无奈的脸,我便开始茫然起来。
[四]
等到山上的花都开之时,便到上学的年龄。
那日我正跟二狗在山上捅蜂子窝,藏在草堆里防蜂子,便隐约听见远处有人在唤我名字“陈阿岗——陈阿岗——”我跟二狗出林子一瞧,原是王家的王胜儿。只见他穿着一身粗布绿色的小衣裳,招着手笑道:“阿岗、二狗,去上学喽!”我问:“啥时候?现在吗?去哪?”他边往南跑边说:“今天去莲花庙上学,快走罢!”
我跟二狗便赤着脚往莲花庙里赶。庙被整修了一番,地上留了几个土坑,想必是被人挖去何首乌留下的,草丛果然见少了,但虫叫声依旧鼎沸。全村子的娃几乎全来了,人挤不动,大部分干脆从墙洞钻过去。最后连墙洞也挤不进去,我跟二狗便只好排在人群后面挨。
我俩许是最后的,教书先生叫我俩报上大名。“陈阿岗”“李文静”。先生一听,从专注的记名中突然惊醒了似的,说:“李文静,你是个女娃罢?走走走,你怎的也来上学?”二狗听了这话,呆了似的无言以对。我道:“咋的?这不是学校吗?先前你也没说女娃不能来。”先生起身,用手甩了甩那件青色粗长衫,又扶了扶黑框圆眼睛,郑重地道:“这学校是什么?按以前来讲,就是私塾。你见过哪个私塾招收女学生?哎,小孩子,不懂规矩,不知道女娃不该来上学呀?”他一壁说着,一壁推着二狗往门外走,然后紧忙地狠狠关死了大门。
我眼睁睁看着二狗和我被隔开了,这次我才真真正正感到我们之间不可抗拒的距离。
待我进屋之后,发现我们全部在一间大房子里上学,庙里的案台改成了讲桌,有金莲的墙也盖了块涂黑漆的木板,先生倒也不怕金莲发怒。先生拍拍讲桌叫我们安静下来,大喊却盖不过这些野娃吵闹的声儿,先生便喊得破了声,也没人理会。他便开始拿着戒尺巡屋,一壁巡还一壁骂:“冥顽不灵,静息,静息,止言止言!――”持着戒尺可劲儿地拍桌子。总算安静下来。王胜儿坐在第一排向我挥手,示意我过去。待我过去后,他道:“这是我给你占的位儿,坐罢。”我道谢后便与他交谈起来。
先生上讲台作介绍,道:“本人姓‘乌孙’,自‘腾’,号‘梓仁’,三十又一,承传孔子之教,兴盛老子之邦,知天文,识地里……”
这时门口的人打断了先生的讲话,是胡乃三带着一个矮娃。我见那小子留着极短的小板头,紫红脸上分不清哪是鼻子哪是嘴,眉毛同头发却是稀疏的,还夹杂着几缕灰白,眼是黑,还是斗鸡眼,青绿色的鼻涕与红脸相互辉映,倒是身上的绒尼黄袄黑裤还较精神,表明他不是块木雕。
乌孙先生迎着村长,村长摆着同样的阔步走的姿势,进了屋,用他那撑不起门面的三角眼环视教室一周,笑着说:“入了学堂,要守本分的规矩,听先生的话,听话!”说罢,就与先生私语了几句,放下小毛子阔着步子走去。
先生好似很郑重地瞅着我们,定夺着什么,便道:“王胜儿,你起身,把位置让给小毛子。”王胜儿不服气,怒视先生,直到看见先生紧紧攥住戒尺,才骂骂咧咧地换到后面去。
就这样过了几日。那天,先生说,要选一位“风雅之首”,我想也就是学子之长,先生选的是小毛子,虽说在情理之外,却在意料之中。但几个哥们儿,特别是王胜儿,很是气不过,便嚷着去找先生去理论。先生却说:“胡阿毛看起来是有点瓜,其实心术很正,负责老实,子承父业,当之无愧。”王胜儿顿时火冒三丈,暴跳起来:“你先前先把我调走,我没说什么,如今却让那个二瓜子当‘风雅之首’,是个君子便不会这般做,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,是……是个糊着金粉的屎壳郎!”先生好似被触着伤痛一样,仓皇掩饰道:“你……你竟如此无理,我作决定哪有你说话的份儿!如此朽木不可雕也!悲哉!悲哉!此若人不配做我的学生……”没有等先生说完,王胜儿憋着红脸,气冲冲地离去了。
自此,王胜儿再也没来过学堂,听说被撵回家,还是村长着手办的这件事。
学了若干日的文化,回去便在二狗面前显摆。起先是教她写自己的名字,尔后教她背诗,或猜字谜。譬如“挣破庄周梦,两翅驾东风,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。”答案便是‘蝴蝶’”。
三年之后,在我学艺渐精时,愈了别人一份字谜给二狗,是这般道:
“天鹅入林鸟不回,
情人驾着云彩飞,
雨后水上一朵花,
过去村庄又一元,
双木非林心相印,
我用两眼看世界,
偶尔有人来相伴。”
谜底是:我会永远想着你。但二狗猜不全,我叫她自己悟去。其实,就算她猜不全,也多多少少明白我的心意。
一日我像往常一样唤二狗去垄上,却被她阿娘吃了个闭门羹,她阿娘道:“如今二狗已长成十一二岁的闺女,离嫁人不远了,你们也应避避嫌,别每天没大没小的,男女授受不亲,日后也不要再写什么字谜了,女子无才便是德,你也明理儿,别害了二狗!”说完便“嘣”的关死了门。
我像害了病似地颓丧的去垄上,发现不远处,有群人挤着看什么东西,我便过去,瞧个热闹。原来是村委会发通知,主要内容是发展大生产,抓住大好时节,勤奋插秧,鼓励生产。只见妇女们一个个都斗志昂扬的撸袖子开始计划一人多少地多少苗。我也不知道政策的核心是啥,就知道大人们都高兴得合不拢嘴,夸政策多么的体贴。
然而政策愈是好,我的心就愈是不安,这是否就意味着二狗是胡乃三的儿媳已成定局。那夜,并不是大暑,而我却觉得燥热无比。我们全家躺在天井的席子上,地边儿的杂草被风吹得“沙沙”乱响,虫子没有眼力价儿的放肆,心里比热锅上蚂蚁还要乱。睡着了,却不安稳,接二连三地做恶梦,我却真正希望那最可怖的噩梦能醒来。
第二天,我去了学堂。上了半截,发现小毛子就是不来,便问先生原委,先生道:“胡阿毛大概是要成亲了。”
“什么?成亲?不就是……二狗!”我惊骇了,没想到噩耗会来得如此之快,便不自主的向后倒退了几步,浑身瘫软在地,真正一次体会到慌神的感觉。“不行,我要救二狗!”我不顾先生的责骂往二狗家跑。
到时,只见二狗穿了平生最花哨的衣裳,是我见过最美的一次。二狗正与爹娘哭着惜别,李东头粗鲁的要撸她上拖拉机,恶狠狠地骂:“臭丫头,麻利点儿!识抬举得快给我上车!”二狗挣扎着:“阿娘救我!我不要,我不要!”二狗阿娘也抓住二狗说:“你们怎的不讲理,不是说入亲吗?这是抢亲啊!我的苦命的二狗,我们不嫁了!你放开她!”李东头和几个大汉拽着二狗不放,一把推倒二狗的阿娘。二狗阿爹上前说:“把礼金给我们,钱呢?”李东头一壁推倒他一壁说:“什么钱!滚!找你的不男不女的闺女做媳妇就不错了,还要钱!”二狗的爹娘就倒在地上无望地哭,认了宿命的捉弄。
我急疯了,像恶狗一样上前咬了李东头的腿,只听他“嗷”的一声,把我踹在地上,踢破了我的头,后便骂了几句,拽着二狗上了车。我听见二狗哭咧的唤我:“阿岗,救我,阿岗……”
我拼了命地起身,去追开动的拖拉机,拿出土枪,不放过任何希望。我边追边哭着唤:“李……李文静……等……我救你……”我的声音越来越虚弱,我身子越来越无力,“扑通”磕在地上,血流了满地。这时,似乎那冗长的字谜成为我俩最后的写照,我们唯一的关系也只剩“想着”;又似乎听见胡乃三最得意的笑,见小毛子鼻涕流到地上荣耀似的快意。
他们的车离得越来越远,慢慢消失在小山路的尽头,我还听见二狗在不停地唤我,但是,这二狗最后的呼唤,也被路旁插秧的妇女勤劳热情的高歌覆盖了,我只听见:“人人都夸济乡好,果蔬满山遍牛羊,自由区呀大解放,满区尽是新衣裳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