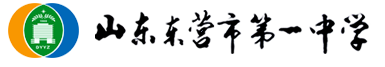那些屋,那些人
发布人:谢鹏娟 发布时间:2008-01-29 点击量:
最近回了一次老家,一不小心,目光又被村里的那些老屋弄疼了。
那些老屋散布在村子的中心位置,散散落落的,周围有些砖瓦房,它们也就显得有些孤零零的。好像从记事的时候起,它们就那样在村子中存在着,又好像它们在不停地变化着。刚开始是屋里住着一个或者两个人——都上了年纪的,后来屋里的人就悄无声息地走了。于是屋子里的人气渐渐散尽——也许在他们还在的时候,这种气息就已经开始消散了。慢慢地,屋顶上长起来一两棵青青的草,与苫着的麦秸的褐黑鲜明地对比着。不知什么时候屋顶上苫着的麦秸就支持不住了,被哪一场风攫走了一把,然后是一片又一片。于是屋的梁就裸露在雨雪中,吹刮在寒风中、暴晒在太阳下了。又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一根梁就在某一个时间里忽然“轰”的一声倒在了屋里,压在炕上,压在灶头上,压在一切它本来为它们支撑起天空的东西上,然后又一根,又一根……屋子就剩下了孤单的四堵墙壁。然而墙壁也慢慢地松动了,先是泥抹的墙皮成片成片地剥落,然后又在某个人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时候一堵墙就坍圮了,墙倒下的时候,甚至溅不起一点儿的尘土,接着就是第二面、第三面、第四面……又一个春天的时候,就在屋子的田地上,就在倒下的墙土上长出了不知名的草,一棵,两棵,越来越多……老屋的院子里也早就是杂草丛生了……
我一直弄不明白,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的儿女们,为什么就不给这些老屋再苫根草,再抹把泥呢?后来慢慢想到,如今他们的儿女们都在忙着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儿女建房子呢,建上漂亮的小院,安上许多扇铝合金的玻璃窗……然而即使这样,村子里的人好像还是越来越少,他们很多都像我一样涌进了城里,虽然也许有的连个像样的窝都没有。
与老屋一样弄疼我的眼睛的还有那些在街头上蹲着或坐着的老人。与老屋一样,好像从记事起,他们就那样在某一个街头存在着。身上永远是藏青色、黑色或深蓝色的裤褂,扣子也总有一两颗与其他的颜色不一样,在肘部或膝盖部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,或者有的老人就那样露着衣服里那满是褶皱的皮肤。当我走过他们时,他们蹙缩起满是皱纹的嘴和脸向我微笑——他们有的还能认出我,有的可能早就认不出了,于是其中一个就说,这是谁谁家的女儿。
我这时总是很局促很惴惴地匆匆从他们身边走过去,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。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很冷的人曾说过,一个人一出世,他的全部未来便明明白白摆在村子里了。
这些人应该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,但又好像有着很多关系。然而,我知道有一个人却确确实实与我有着最亲近的关系,这就是我的奶奶。
奶奶去年跌了两次跤,第二次的时候,便瘫在了床上,左半边一动不能动了。自从奶奶不能起来后,爷爷就再也不能离开奶奶半步了。只要爷爷一离开,奶奶就不停地大声呼喊爷爷,于是,村子里就经常回荡着奶奶长一声,短一声的呻唤。
于是,每次我回去的时候,奶奶都会皱着半边没有知觉的脸口齿不清地跟我唠叨,她说,她浑身疼,像许多针扎着似的疼;一个姿势躺累了,换个姿势时,都得爷爷把她抱起来,慢慢转过来,即使这样,也还是疼。奶奶不止向我说,她向所有去看她的人诉说,渴望在向我们诉说的时候疼痛能够减轻些。但我知道,奶奶依旧疼着。
就像刘亮程说的,隔着三十年这样的人生距离,他能感觉到母亲独自在冬天的透心寒冷,但他无能为力一样,我能感觉到奶奶的痛苦,可是我更是无能为力——我与奶奶隔了整整四十八年啊!
离开的时候,我没有去跟奶奶道别,我不敢,不敢面对将别时奶奶的脸,还有她即使不说,也能感觉得到的对生命的未卜的凄惶!
走了,走出村庄时,我回头望了一眼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,发现从这里看,这竟是一个簇新的村子,满眼的红砖红瓦,甚至还有一两座小楼。
然而,我知道就在村子的中心位置,还有许多老屋,他们将永远矗立在寒风中,矗立在我的记忆里。